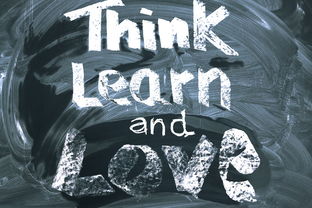(受访者提供/图)
“咱们多提节目。”马东又重复了一次。他已经很久没以个人名义接受采访了,有关他的曝光都以“米未”的形象出现。他形容自己是米未的“幌子”,就像酒馆外面挂的旗,在阳光风雨里招摇,先于饭菜见到客人,主职是迎来送往。
采访中,他不止一次强调“个人表达没有价值”,而做节目像熬粥,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料,但合在一起只会熬出一种味道,无法辨别哪个味道来自谁。
在米未公司走一圈,到处都是熬出的“粥”。进门的立牌上写着米未的使命、愿景和七条价值观,由员工集体讨论确定。它们还出现在每一间办公室的电视屏幕上。每年做什么节目,也由核心员工讨论决定。米未内部的“死亡清单”上,很重要的一条是“如果我们的决策是来自于单一的来源,那就意味着死亡的边缘”。
公司里,除了几位老板的办公室,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名字,同样由员工提名投票产生。多年前,米未让员工提名自己最快乐的时刻/地点,于是迪士尼、布达佩斯、马达加斯加……出现在了办公室的门牌上,采访时我和马东所在的房间叫“杠上花”。
十年前,马东一手打造的辩论节目《奇葩说》算得上“横空出世”,接下来几年,米未出品的《乐队的夏天》和《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一经播出即成为年度现象级综艺。马东的故事也随着这些节目的走红而广泛传播:相声大师马季之子,1980年代末留学澳洲,30岁开始做电视节目,当过春晚导演,离开央视进入互联网行业,从爱奇艺离职创办米未传媒。
在种种叙事中,马东努力贴近年轻人,温和又素雅,幽默也狡黠。穿得花里胡哨,流行语挂在嘴边,跟团队做的每一个节目都能挂上热搜……这个形象与各个节目一起越熬越浓,于是,米未变成“里子”,马东变成“幌子”,出来讲话,“米未”既是任务也是披挂。
“好奇”是他现在愿意展露的部分:数码产品永远是最新款,新上线的游戏都会玩。热衷于在最前沿的技术和学科中打转,最近关心的话题是脑神经科学与AI的结合。
但如果再想往他心里挠一寸,他马上摆摆手,宣告此路不通,再把“米未”披在身上:“不是马东的意见,是米未的意见。我从来不觉得个—人—表—达———(四个字拖得很长)有价值”。
2024年9月,喜剧竞演综艺《喜人奇妙夜》终于收官,这张“幌子”又在一阵热闹中被挂出来,招呼媒体。
《喜人奇妙夜》“喜奥笑”运动会录制现场,左起:王建华、高颖、高越、马东、罗圣灯、酷酷的滕(受访者提供/图)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马东的对话。
作品比的是穿越时间
南方人物周刊:
2021年、2022年,米未做了两季《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以下简称《一喜》、《二喜》),2023年做了《乐队的夏天》(以下简称《乐夏》)第三季,今年为什么又回到喜剧赛道,做了《喜人奇妙夜》(以下简称《喜人》)?
马东:
做《乐夏3》是因为喜剧节目还没有准备好。做喜剧节目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培训,这个过程中导演团队不能空转,刚好《乐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累,有一批我们心中想要的乐队出现,就水到渠成去做了。《乐夏3》做完,《喜人》的筹备和前期培训也进行得差不多。
同样是喜剧类综艺,《喜人》在筹备过程中跟第一季、第二季相比是更顺还是更磕绊?
一模一样。既没有更顺,也没有更磕绊。我对时间不敏感,那天听到刘琪(编者注:《喜人》选手)讲他们第一次来米未接受培训是2023年3月,现在节目播完了,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18个月。整个筹备期还是会有这么长。
《一喜》做完了开始准备做第二季,我在开全员会,拍了自己茶杯的照片,讲什么叫“空杯”:得把杯里的水倒掉,才能盛下一杯水。如果不空杯,老带着“我曾经做成过什么”或者“有些事情我尝试过但没有做成”(的想法),很难有突破。当然从实际情况看,或多或少还是会留个茶底,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不提醒不行,要是不倒掉更麻烦。
所以你要问我,我会说越来越难。选手们会总结方法,觉得只要这样就容易获得好成绩;如果那样,再巧妙的现场效果也不会好。导演组也会觉得只要往这个方向来,驾轻就熟,就能尽快出作品,能够完成KPI。如果新开发一个(思路)也可能面临失败的风险。总之就是升级打怪,每天面对这些事儿。
套路化的思维怎么面对?
不停地对抗“熵增”,虽然这个比喻不严谨。对抗“熵增”就是打开系统,不停往里掺水。“熵增”是封闭系统里的自然现象(编者注:可以理解为“总能量不变,但可用部分越来越少”),要打开就得不停往里面扔新的,但又不可能全换掉,因为核心团队的经验积累在,选手的培训费用成本巨大。
新的演员培训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是天然的新的要素。在制作的基本盘里,我们确实有很多新的尝试,比如跟刘天池老师的合作,跟不同的编剧的合作,这本身就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
为什么在喜剧系列的节目里好像特别重视编剧这个群体?
对于我们的生产来说,编剧是重要的一环,他们应该被人看见。你可以说(特别重视),但是我愿意说我们更重视共创,而不单单是重视编剧。因为大家天然地觉得他是编剧,他是演员,那个人是导演,凑到一块,各司其职,就能够把这些事弄好。不是这样的。
它不是一个机械运行的过程,齿轮转了自然就出来了。它是熬粥,一把米、一把黄豆、一把红豆,还有不知道什么东西,搁在一块儿乱炖三天三夜,最后出来的时候有丰富的味道。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分出这锅粥里边到底哪个是黄豆,哪个是绿豆。
《喜人奇妙夜》决赛录制现场,左起:贾冰、秦昊、沈腾、徐峥、黄渤、大鹏、马东(受访者提供/图)
《喜人》的初舞台上很多作品是选手们打磨了很久才呈现的,但进入正式赛段以后,不到一个月就要呈现一个作品,长时间打磨的与很快完成的作品会有很明显的差别吗?
当然会有。我们的内容逻辑叫“智力总投入”,指足够长的时间、足够多聪明的人放在一起。多熬一会儿肯定更好,但具体是不是越长越好?我们也经常看到有些作品就放着,放凉了也确实有。
创作者很奇怪,跟他说咱们有九个月的时间,用前三个月做一个,中间三个月做一个,后三个月做一个,这样在数学上看起来很合理,但实际上不会,他一般会用八个月的时间做完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根本不会去想,因为没脑子想了。人的思维惰性就是愿意在已经有把握的事情上多想,重新去烧脑,开另外一个东西,不把我逼到那分上我不会干。
艺术创作一定是拖延症(发作)的过程,最后不拿“枪”顶着不会出东西。我们尊重这个规律,又想做边录边播的模式,因为更生动,播出效果和反馈、跟观众的互动能够回馈到节目里,是一个飞轮。既然要做飞轮,就要忍受后面的强弩之末。
你之前提到你父亲马季先生每做一个节目可能准备半年多,上去只演个十几分钟就结束了。类似《喜人》这种,不管是长期筹备还是强弩之末出来的作品,都是台上演完就结束了。
他有的写半年,有的写俩月,但甭管写多长时间,只要上了电视就八分钟,然后就完事儿。但是它永远会留在那儿。很多春晚的相声小品,今天还会有人拿出来看,《喜人》在播的期间,第一季和第二季的很多作品,流量也在增长。
喜剧有一个特点:它的长尾效应特别好。观众会不停拿出来看,甚至好多都会背了,还是会看。喜剧天生能帮助人放松,获得多巴胺。有时候已经不是为了获得新鲜的爽感,而只是为了获得当初爽感的记忆,因为记忆本身也会产生多巴胺。有个小鼠实验,它摁一下键你给它吃一块糖,摁一下吃块糖,后来它摁一下不给糖,但是它摁着也很高兴,就是这个道理。
《喜人》这些作品出来之后,看《一喜》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像《笑吧,皮奥莱维奇》这些作品都被重新拿出来讨论。
这个是合理的。不管当时有什么样的播出效果,没看过的人一定更多。所以很多人是因为看到了《二喜》才知道有这么个节目,再去追追第一季。有好多人看到《喜人奇妙夜》,会去追两季喜剧大赛。
但是会有一个评价的变化,比如说《一喜》某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可能口碑没有那么好,但是现在观众会说《一喜》的某个节目很好看。
经典的产生未必在出现那一刻就石破天惊,有很多石破天惊的东西很绚烂,但是就过去了,像烟花。有很多东西越看越觉得好。我觉得土豆、吕严的《大巴车上的奇怪邻座》就非常好,当时有很多人看不懂,他俩都被淘汰了。今天回过头来觉得,哇,真的好。内容产品最后比的就是穿越时间,不是那一下多么绚烂。我现在还是会重看好多老电影,也是一种自我安慰。
《喜人奇妙夜》录制现场,郭甲醛(左)、闫佩伦(中)、孔令美表演《我来咯》(受访者提供/图)
喜剧创作方法论:Yes,and……
米未从做《乐夏》转向做喜剧,算是倒空茶杯的叙事吗?
今天给自己找来龙去脉,会发现我们的喜剧元素一直很多,比如《奇葩说》和国际大专辩论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奇葩说》可以看成喜剧版的辩论赛,辩论的东西和表演的东西各一半,甚至喜剧成分占得更多。米未的内容基因里,喜剧的成分特别大,我们对喜剧天然敏感。我们开始想做情景剧,建组了,投入了时间和团队去筹备,发现不行,交代不过去,解散了。就这样重复有两三次。这个过程中做了《乐夏》。
我们发觉积累学习还没到,开始去学习sketch(编者注:素描喜剧)、学习共创,请了外国老师来教我们即兴创作,这些东西都学完以后,我们把能力范围内最驾轻就熟的综艺形态和喜剧先放在一起,做了《一喜》。
之前你提到,《乐夏2》结束后,团队在纠结做《乐夏3》还是转向喜剧节目,合伙人分成两派,各执一词,看谁能说服谁。
对。当时《乐夏3》是一个更容易的选项,顺势往前。但其实《乐夏2》做到后来也很辛苦。
我们所有事儿都需要争吵才会有结论,如果大家就一件事儿出奇地一致,我们先天地会怀疑这件事儿有问题。我们相信只有不同意见进行充分交流、取舍和判断,才更能规避风险。这是一个习惯动作。吵的过程让大家更清晰,做的时候也不用再纠结。不会有“你看我当初就说了别这样吧!”之类的话出现。有了结论,所有人义无反顾照着那个方向去做。
在我们所接触的节目形式里面,喜剧是最难的,《乐夏》容易一些,是因为那歌是人家写好的。人家花了15年就写了四首歌,全在节目里唱了,我们只是怎么去包装它。像《鲜花》那些歌本身就好听,喜剧难在每一分钟原创的东西都是我们的。不过做完喜剧我们也逐渐坚定了我们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
2023年8月10日,《乐队的夏天》第3季举办开播前的媒体看片会。MR.Miss乐队、二手玫瑰乐队、回春丹乐队、瓦依那乐队和主持人马东(右一)合影(视觉中国/图)
这几年的喜剧节目最终的呈现形式也是争吵的结果吗?
我们最开始只知道共创是生产喜剧的好方式。以前的喜剧节目是腕儿的艺术——一群喜剧明星聚在一起,憋得眼睛发紫,好不容易弄出一个来,下一季再也不做了。整个喜剧的创作过程就是这样,投入大、不确定性强。
所以我们找到了共创这个模式,任何10个人里面,只要经过培训,都能挑出四五个人来,通过随机的共创、通过“yes,and……”让一个点逐渐完善。我们先发现了创作规律,以创作规律为原点去搭建整个节目和喜剧作品。它不是我先想好了,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
怎么接触到“共创”的?
我们想做喜剧,就开始了解全国、全世界的喜剧创作,去研究这东西都是怎么来的,看到很多人其实都有过在海外短期读喜剧培训班的经历。我们早期的培训老师都是海外过来的。
海外整个喜剧的模型,基座就是我们熟悉的单口喜剧,不是上电视那种,就是在各种酒吧里边、学校里那种单口喜剧。这些人需要去接受培训,他们有几大喜剧学校,有各种各样的课程,可以上一个两星期的,也可以上一个四年的,学创作方法、表演方法。如果自己有写作能力,掌握了一些基本技巧,就能以写单口喜剧谋生。这个系统往上走,就进电视台去主持晚间节目。原来的《周六夜现场》都是这样出来的,这个系统已经很多年了。再往上是情景喜剧,《六人行》《生活大爆炸》……这些剧里面的很多人其实就是喜剧演员,再往上走可能是喜剧电影。它的金字塔结构非常鲜明,底数特别大。
整个系统的搭建和核心的培训都是共创。每个社会不一样,马东:幌子的快乐需求不一样,但是这种创作方法值得学习。
现在各种类型的喜剧越来越多了,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的喜剧作品没有那么冒犯。而冒犯是引人发笑的点。
一定要冒犯才有喜剧吗?我听万维钢(编者注:科普作家)的课,其中一期讲什么是幽默,他就说幽默是一个人人都熟悉的概念,但是很难把它总结出来。
我们这一代做喜剧的人,都认为幽默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万维钢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说他觉得这是一个结果论,但没有办法指导创作。然后他提到了西方人有一个对于幽默的概念,叫作幽默是温柔的反抗。我当时听了以后也想半天,到底这个对还是不对?
我接受一半,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准确的描述。但是他是不是一个前置地能够指导创作的(概念)?它跟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是一样的。我觉得都可以听听,这也是很聪明的一种总结。所以你说的喜剧中的冒犯是不是反抗的那一部分,我也不知道。只是在我心中,如果说只有通过冒犯才能获得所谓的喜剧效果,我不认同。
那《喜剧大赛》和《喜人奇妙夜》的幽默来自哪里?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没有答案。我的世界观里面对所有复杂问题都没有办法给一个简单答案去概括。我觉得身体是诚实的,你去看,你乐了没有,你想看不想看?你放弃评审的眼光和当一个理论家的企图的时候,不喜欢看就过,喜欢看就看,看完了还想再看一遍就再看一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喜剧创作中,“yes,and……”有跟共创一样重要的位置?
这个是创作方法论。比如咱俩坐在这儿,就会产生竞争。在交流过程当中通过对抗去确立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但“yes,and……”是希望能够在大脑里先放掉这个东西,无论怎么样,我们现在只在说Yes的前提下进行。以前做辩论其实就是“no,but……”,不管说什么都是no。“yes,and……”即便是一个极其荒诞的开始都要进行下去:“这张(白色的)桌子是黑的。”“对,你看它黑得多么有光泽,它的光泽看起来都显得有点发白。”“yes,and……”是一个递进逻辑,没有对错,甚至连逻辑都不讲,只要能够升番就行,它的目的是为了升番。这个是喜剧创作的方法论。
我们以前没研究过,所以也没接触过。
200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彩排,马东(中)和四位搭档表演群口相声《五官新说》(ICphoto/图)
掌握了结构能力,就能吃这碗饭
现在做喜剧节目跟你从小耳濡目染接触到的喜剧有什么不一样?
没什么不一样,但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喜剧。从喜剧的作用角度来看,它就是为了让人在大脑当中产生神经递质,产生了就对了。
但是它跟社会环境有关系,比如说我父亲1974年说第一段相声,那时候社会上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相声。我父亲1956年进广播说唱团的时候,中国南北方语言还不通,他们进广播说唱团的核心是为了把普通话推广到南方去。我们已经忘了,但其实这是很近的事,就是80年前。南方人和北方人见面靠语言是不行的,但是中国人文字是一样的,你会读书,咱俩就可以交流。
观众快乐的阈值有变化吗?
也许会有,但这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我经常听到别人说逗笑今天的观众太难了,因为他们什么都见过。这可能就是你说的“阈值”。但是他们还是会被新鲜的东西逗笑,而那新鲜的东西也是人脑想出来的。所以每一代创作者面临的阈值问题在本质上一样,大家的情理不同,但是意料之外永远能让人发笑。公平之处在于在这个时代,你跟我一样,咱俩面临的情理之中一样,比的是意料之外。那也往前推30年,肯定情理之中就不一样,但是同时代人面临的问题一样。所以我觉得不要去想说今天的人太难逗笑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20年前的春晚小品,还是会笑,但我们的情理之中已经变化了。
2009年春晚,《不差钱》里小沈阳出来的时候,他说:“这个可以有。”确实是意料之外,哄堂大笑。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词儿都背下来了,其实是回顾和温暖,今天看《卖拐》你不会因为你背下来了就不笑,还是会回忆当年的快乐产生的多巴胺。
所以如果今天一个小孩第一次看《卖拐》,他不一定会笑?
还是会笑,因为里面的结构。里面有些词他可能听不懂,比如“忽悠”,当年所有人都知道是什么,今天说“忽悠”已经觉得这个词很out。我小时候,相声里写一个“盖了帽”都会哄堂大笑,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盖了帽。这个是语言的流变。但是结构还是会让人发笑,百试不爽,谁掌握了结构能力,就是我们讲的叫作“天生是吃这碗饭的”。有的人天生幽默感不足,一屋子人一人讲一个笑话,就他讲完了以后谁都没笑,那可能就不适合干喜剧。
所以做喜剧还是要天分?
肯定要。我们所做的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茫茫人群中去找那些最有天分的人。
综艺都是生意
梁龙回忆去《乐夏》的经历,那个时候他犹豫要不要参与,跟你聊天,说担心播出效果不好,然后你给他回的是:“我们要往更大的方向走,未知的风险谁也控制不了。”更大的方向指的是什么方向?
我在忽悠他们(笑)。不是,艺术家是这个世界上最缺乏安全感的一群人,因为不知道明天的创作是什么样,明天的市场是什么样,不知道能不能够被别人接受,一首歌出来别人不喜欢怎么办?他们先天需要鼓励,需要给他们营造安全感。
梁龙下决心来《乐夏》之前,我们费了很大的功夫说服他。他很实在地跟我说:以后会怎么样?会不会播了以后反而不好?
我跟他说的是实话啊,我哪能知道好和不好,但是总的来说所有上节目的人,只要你的歌好,只要你好,从长远来看都是好的,播出第二天,1000万观众看了有50个在网上骂你,你这日子就甭过了,你会盯着这50个人不停想跟他们PK。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要往前看,往大的方向看一定是收益大于成本,短期内会不会有成本谁也不知道。
你们做节目也是这个逻辑吗?
当然了。世界上所有的生意面对的都是未知和不确定性。我们特别讲究概率思维,每一个决策都是赢面更大一些,相对有把握了就去做。
所以现在做综艺做节目对你来说都是生意?
当然。肯定得是生意,不是生意,怎么能持续做下去?正因为它是一个生意,才能够保证收益,能够维持这个团队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创作当中去。
全公司上下一百多人,节目运行期间还不止,所有的演员在这儿排练、培训、演出,这些都是成本、都是钱,如果不挣出来怎么弄?
有没有不是生意的部分,有个人的情怀或者兴趣的部分?
有我也不会告诉你,因为那个东西没有意义。我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保持这里可持续运行,所以它对我来说是生意这一部分更重,优先级更大。把我们所有人的情怀都满足了,然后干不下去了,有什么意义?活不下去了,就都没有意义了。如果为了满足自己ego(编者注:自我)和一时爽,付出了长期价值的代价,第一是愚蠢,第二是自私。
马东怎么想不重要
你一直在强调贴近年轻人,节目越做越多,最早一批观众的年龄也在增长,现在希望继续吸引更年轻的人参与,还是跟着这一拨观众一起成长?
我们在《奇葩说》第四季和第五季的交界时面临困惑,观众从20岁开始看《奇葩说》一二三季,他们对《奇葩说》的要求就变成了需要更高精尖,但是其他的人就看不懂了,而有很多18岁的人长到20岁了,他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需要启发,所以到第五季我们就回过去做,我们当时叫“做人身边的道德困境”。
今天喜剧之所以让我们觉得是有长期策略价值的方向,正因为它有点老少通吃,《一喜》我有好多朋友的孩子,才七八岁,能背下来,他甚至有很多事根本就不明白。我三岁听快板书,听三遍我也给背下来,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喜剧是一个蛮长线的生意,但确实是最难的。
在喜剧的方向上去持续发力,是我们的既定方向,我们是一家喜剧内容公司,只是这种内容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努力深化积累学习喜剧的创作方法论,把它外化成某种产品形态,那是它的自然结果。
《奇葩说》时期我们没有明确喜剧的战略,只是觉得我们即便要做一个辩论,也可以做得好玩。没人会朝着不好玩的方向做节目。我以前做《文化访谈录》一点喜剧成分都没有,但我认为里面的价值也很好玩。对我来说是好奇心的满足,虽然一点都没有打岔,也没有包袱,但是我很喜欢。
至于我们的产品是不是有某种调性,千万记得这不是马东的选择,不是马东想要的和得到的。本质上马东只是米未的一个幌子,像一个酒馆外面挂一个旗,核心是我们的创作团队,只是他们面对不了记者,就把我派出来。你可以说采访的是马东,但是本质上所采访到的内容和得到的观点是马东代表米未的一种表达。
这个过程中马东个人的意见会占多大的比例?
在熬粥的过程当中就混在一起了,消化掉了。也许我只是鸡精或者是姜,姜是老的辣的,而我是这里面岁数最大的。但味道已经无法识别,也不重要。
这是你主动的选择还是团队的放置?
是PK的结果,我PK不过他们就只能接受。或者这样才是聪明的选择。如果这个公司是一个人说了算,那出错的概率就会更大,死的概率就更大。
我们有一个“米未死亡清单”,来自芒格的那句话,你最好知道你死在哪,这样一辈子都不去那地方。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如果我们的决策是来自于单一的来源,那就意味着死亡的边缘。这个在内部公开,尤其是管理层。里面还有不通过贿赂获得商业机会。
是什么让你发觉个人决策对公司的致命影响?
岁数。活到这么大了,见过所有一开始欣欣向荣的公司,最克制不住的东西就是创业者、领导者、决策者的ego:因为我做对了决策,所以就一直觉得我说得对,你不要反驳我。往往就死在这个上面。
我们每一个项目结束了都有非常“惨烈”的复盘,所有人哭成一片。每个人面对全公司去讲一两个小时,当时这件事儿我做得好的是什么,做得不好的是什么,难处在哪里,委屈在哪里,击穿到灵魂深处。
因为整个导演组都面临巨大的压力,无数个见天亮的日子,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负能量,需要被看见,同时也一定会因为情绪而产生很多错误的判断,所以把这些东西重新翻出来看,其实有利身体健康,它的实质作用就是精神按摩,不然处在巨大的内耗当中没有下一次。我们相信这是成长,不成长就会掉队,就会离开。
我们马上要九周年,每年我都会定一个主题,今年主题是“安住于心,全力以赴”,“安住于心”是我在过去的一两年里所获得的成长,怎么样通过学习和思想反省,能够和自己在一起、和当下在一起,让所有人在这个层面上进行交流。
当所有的行业都面临巨大不确定时,会有天然的恐惧和贪婪。贪婪来自ego的膨胀,想获得自己不配拥有的东西;恐惧来自于对未知的过度担忧,会使自己畏首畏尾,失去正确的动作。恐惧是个悲剧思维,为什么叫安住于当下?岁数到了就知道世界上再不好的事情,第一当它要发生的时候,你拿它没办法,天塌下来个大的顶着。第二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35岁的时候,想说人的预期寿命是70岁,今天我人生过半,这后半辈子怎么弄我得想想。但过了那个阶段,现在我56岁,生命总有一个终结,越靠近恐惧就会越小,因为没有那么多可失去的东西。
所以跟当下在一起的核心是看见自己的变化,也是克服恐惧的一个方式。古今中外那么多大聪明都是这一条路,一定有它的道理。
为什么这两年才获得了这个想法?是因为经历了ego的膨胀和贪婪吗?
肯定有。今天回想起来确实还是幼稚,但那是个必然过程,是鼓舞。安住于心是今年的感受,明年有明年的感受,这就是成长。
《喜人奇妙夜》总决赛合影(受访者提供/图)
我从来不觉得个人表达有价值
之前你提到过“中道”的概念,做到这一点难处在哪里?
不偏不倚谓之中,但是偏和倚是人的本能,站在中间需要巨大的能量,就像站在平衡木上,为了保持平衡,需要全身使很大的劲,因为自然状态应该是掉下去,要对抗地心引力。之所以说它是一种追求,是因为需要做功,需要很大的能量和付出,才能够也许保持在这条路上,人特别容易偏颇,这个顺乎本性。所以保持中道是一种修行。
你在不同阶段的节目中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是逐渐修行的过程吗?
那是因为干的活不一样。不同节目的目标不一样,我在其中承担的功能也会有区别。
所以其实你的个人意志在这些节目里都……
都不一样,但都不重要,我特别怕个人意志。
我想做一个节目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但是这个节目做出来是什么样,不可能是我个人的自由表达。今天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会去跟你讲,其实个人表达没有价值。当然今天很多节目、很多人在追求个人表达,我也很愿意看,但是我不愿意去做。因为我觉得个人表达没有意义。
但《奇葩说》是一个很个人表达的东西。
是吗?我不知道。如果看的人觉得是辩手的个人表达那也挺好的。《奇葩说》是一个舞台,我们搭建了一个关于观点的游戏舞台,开杠的舞台。既然要开杠了,鸡蛋里也得挑出骨头来。我不知道你看了以后什么感觉,我只能确定一点:没有一个是节目组想表达的观点。节目组只想做一个好看的节目。
我看到你之前说过,米未想做的是找到有才华的人做有趣的事情。这个过程也不算自我表达吗?
应该是我说的,我承认。但我忘了这句话哪来的。这句话也不重要,就是对我来说从来就没有想过“个—人—表—达—”这四个字。在我看来这个人有特色,他能够站在一群人里面被看到,这个人就是非常有特点,至于他的特点是不是通过“个—人—表—达—”的渠道展现出来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而且我也不觉得“个—人—表—达—”真正有所谓社会层面的价值,我只是觉得节目有市场和生活当中的价值。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这件事:我压根就没想过个人表达。
为什么你经常强调正向情绪价值?
正向情绪价值,是我们培训时请了一个脑神经科学的专家,讲人的大脑的运作机制。我们才知道“情绪价值”。现在这个词被用“烂”了,但是我们确定这个词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什么人用。当时对这个词的理解就是它是脑神经递质,而不是今天所说的安慰剂效应。所有的情绪价值都会使你大脑产生神经递质,但我们想做的内容就是产生多巴胺、内啡肽,让观众产生好哭好笑的感觉。
这个事之所以写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是因为它经常容易被忘却,但其实要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一个内容产品,是一个没有实体的东西,它是一堆电信号,电信号通过传播渠道,产生价值的终端是人的大脑,在那产生价值。
生产技术的进步会决定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决定着内容的形式,但是我们做内容的人一直坚信的那句话叫作“内容创新的本质是突破内容的形式边界”。
你觉得快乐可以制造吗?比如说做一个节目,整个过程算是制造快乐的过程吗?
不是,我们只是在制造节目,快乐是这个节目在观众大脑里面的神经反应。快乐是我们的目标,但是不能直接说我们在制造快乐,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你最近一次开怀大笑是什么时候?
我天天都开怀大笑。我还是一个会笑的人。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张明萌
责编杨静茹